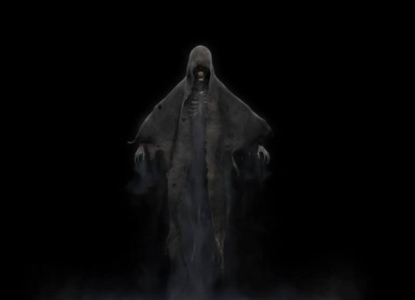40年代发生的灵异惨案纪实:海河惊现300浮尸 诡异的是死因各不相同
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场灵异惨案,海河莫名惊现数百具浮尸,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起初,人们以为是天灾或者冤魂索命,然而,经过当地警署和有关部门的调查后发现,这起事件的幕后真凶竟然是侵略我国的日寇,日本侵略到底做了什么?这数百具浮尸又从何而来?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号称民国八大奇案之一的海河浮尸案。
1936年5月1日清晨,天津大直沽附近海河岸边散步的人们无意间发现,河中心晃晃悠悠地飘荡着一具尸体,起初,老百姓们以为是不慎失足跌落的倒霉蛋或者是被地主压迫,想不开跳河自尽的苦命人。
然而,正当大直沽救生会的成员打捞尸体的时候,更多的浮尸从上流飘了过来,一眼望去至少有十几具。
而将这些尸体悉数打捞上来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些浮尸大有来历。
根据仵作检查后的结果显示,这些浮尸有大致三种由来:一种是近期溺亡的新鲜尸体;一种是早就被淹死,尸首严重腐烂的尸体;最后一种则是在死后被人抛尸海河的尸体。
其中,第三种尸体的数量不仅多,而且死亡原因各不相同,千奇百怪,以那个时代的科技技术难以追根溯源,这也为该案件平添了一层诡异迷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清晨都会有新的浮尸在这一带被人发现,这些浮尸仿佛是被人安排好的一样,按时按点顺着河流从上游飘到下游的海河口。
数量之多,看得人毛骨悚然。
随着尸体数量越来越多,关于这些尸体的来源也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水鬼集体索命投胎;也有人说,这是蛊毒瘟疫所致;更有甚至扬言,此乃天罚,不久之后必有大劫。
一时间,谣言四起,整个天津城人心惶惶。
而根据目前能收集到的报纸资料显示,从1936年5月1日到5月8日,这8天时间里,一共发现了67具浮尸,而在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浮尸数量有增无减,从67具扩大到了300多具。
这无疑加剧了民众间的恐慌,为了安抚民众,也是为了查出浮尸从何而来,天津市警察局及五河水上警察局联手对此事进行调查。
5月14日,三艘汽船在接到任务后,分给开往南北运河跟大清河,检查上游是否还存在浮尸。
如果上游存在浮尸,就在当地直接打捞并调查尸体来源,避免更多的尸体飘到人流密集的下流,制造恐慌和瘟疫。
然而,令船员和警察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三条运河正逢旱期,河水极其的浅,最深处不到两米,根本淹不死人,就更别提发现什么尸体了。
如果这些尸体不是从上游来的,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天津市警察局怀疑,这些浮尸可能是从天津市区的某处地点被送丢弃到海河口里的,为此,他们派遣了大量的人力去天津市各地逐一排查来源,而五河水上警察局这每天派遣自行车队沿河岸巡逻,寻找海河浮尸的源头调查其来源。
2天后,警局传来新的消息,负责调查尸体身份的警员发现,这些浮尸的身份大多卑贱低微,绝大部分都是吸食过白粉的乞丐,并且这些乞丐的尸体身上,有程度不同的伤痕,初步推断是互相残害所致。
仵作推断,这些乞丐可能是半夜毒瘾发作,被打得不能动弹的人,就被人脱衣捆绑推入水中活活溺死。
这个理由看似合理,但却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那就是凶手为何对他们下手,难不成单纯是因为觉得好玩?
而且就在当天,人们两次在海河附近发现浮尸,分别是清晨和下午,浮尸数量皆为7具,而且这次的浮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就这样,仵作的推测被现实啪啪打脸,而海口浮尸也成为了当时的灵异悬案。
由于警方毫无头绪,再加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出现浮尸,这起案件也随时告一段落。
1937年4月,日本逐渐脱下了伪装,全面侵华的态势逐渐明显。
也正是在此时,平静了不到1年的海河口上再度出现大量的浮尸。
而这次则跟一年前的情况略有不同,有老百姓表示,亲眼目睹这些浮尸是从金刚桥那边飘来的,而在仵作对尸体进行解刨后发现,这次的情况和之前几乎一样,尸体大多都是吸食了毒品的底层人士。
而在收到这一线索后,警方再度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活动,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调查后,1937年5月8日下午15点,天津警察局终于在龙王庙毗邻日租界发现了重要线索。
就在当时的电话二局后门的夹道里,警方发现了大量的吸食白面的乞丐,他们的衣着和状态与浮尸几乎一样,几名警员决定就地留守调查,果不其然,在当天晚上就发现有人正在搬运几具乞丐尸体。
警员们迅速出击,抓捕了两名抛尸者和一名尚有一丝呼吸的尸体”,根据二人交代,他们是受人指使把尸体转移到海河河边,但却拒绝承认是他们把尸体丢入海河。
这与警方发现海河边存在尸体的情况能够呼应,却依旧无法解释,为何每天都会有大量尸体被丢弃。
而且,就在他们被抓的第二天,大直沽海河口又发现了三具尸体。
显然,这两人只是不小心漏网的小鱼小虾,真正的幕后真凶另有其人。
很快,天津警察局发现,日租界里存在重要嫌疑,一名天津警局的警员无意间发现,天津日租界的报道显示,从4月6日到5月10日,一共发现了36具浮尸,然而实际情况却是93具。
除此以外,日租界还以整理社区容貌”为由,大量搜捕乞丐,这些乞丐的下落无人得知,这让许多人把目光投向日租界,这里面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天津警局当即派遣多名警员企图对日租界进行调查,然而,由于当时的一些时代原因,日本人在中国的权势极大,警员们根本无权进入。
就在警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在警员们抓捕两名抛尸人的时候,还意外救下了一个尚存一丝气息的乞丐,而经过医院多日的抢救和治疗,这名乞丐也在不久前苏醒,警方立即找到他进行审讯,这才从他口中得知了日租界的惊天秘密。
根据这名乞丐的介绍,警员们得知他和其他乞丐一样,原本都是从全国各地到天津日租金打工赚钱的打工人。
但在进入日租界不久后,他们就从日本人口中得知,日本人开设了一个休养地”,在这里不仅有美女和赌场,还有数不尽的鸦片和海洛因,只要你有钱,就能在这里当皇上,享受任何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快乐。
许多打工人受不了诱惑,把辛辛苦苦打工换来的血汗钱,全部投入了休养地”里,终日吸毒,最终沦为了乞丐。
而这名乞丐所能记起最后的事情就是,他从一个日本女人那里买了一袋海洛因香烟,但在抽过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根据这名乞丐的交代,天津警察局立即向上级申请了最大权限,并对日租界进行调查,而查到的真相,令所有人都捏紧了拳头。
原来,海河浮尸中超过七成的尸体,都是日本人在日租界经营的毒品市场的牺牲者。
日本人哄骗当地人和前来打工人吸食鸦片海洛因,并且他们还在这些毒品中掺了其他神经毒素一般人吸食之后,便会失去意识,严重者会窒息而死。
而在这些人死亡或失去意识以后,日本人就把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扒光,然后再打包扔进海河。
由于这些吸毒者大多失去意识,因此很快就会溺毙而亡,而那些尚有意识的人,也会因为毒品的残害无法游回岸边,最终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迎来死亡的结局。
更令人发指的是,到了冬天,海河口结起浮冰,这些日本人就偷凿冰窟,把数以百计的吸毒者和各种毒品残渣一并丢下去,尸体会随着浮冰下的洋流一起被漂入大海,而被发现了海河浮尸,不过只是大批牺牲者中的冰山一角。
靠着夺取这些吸毒者身上的钱财,日租界谋取了巨大的暴利,而这些暴利也正是支持之后日本全面侵华的经济来源之一。
此时,或许你以为这就是海河浮尸案的全部真相,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在这个真相背后另有蹊跷。
根据后来出版的《解放周刊》所披露的资料显示,这些被日本人丢弃的吸毒者大部分其实都是幌子,在这背后还有另一个令人发指的秘密。
1936年,天津的日本侵略者修筑了河东东局子兵营,之后又在次年修筑了津东李明庄兵营,而这两个兵营在之后,都成为了日军侵华的重要据点之一,为此,日军招募了一大批中国劳工,为其修建炮塔和防御工事。
而在竣工之后,日军为了节省资金和封口,直接将这些中国劳工打晕或直接杀害,然后用他们修建的大型地下管道系统,把他们冲进海河活活淹死,除此以外,日本人还通过非法手段杀害了当时位于日租界的一些中国权贵,并把他们的资金划入自己的账务,而尸体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处理。
这就是为何,海河浮尸有那么多年龄身份性别各不相同的尸体的原因。
然而,尽管天津警察局尽力破获了这起案件,却碍于各方原因无法逮捕涉案的日本人。
为此,他们只能委托天津和河北的市政府,建立一些廉价的收留所,尽可能招收四方各地而来的劳工,让他们从事一些简单的政府工程,并命令禁止所有中国人进入日租界,以此保证当地老百姓和劳工们的人生安全。
现如今,海河浮尸案早已过去数十年,日租界也和日本侵略者一起被那个时代的无名英雄们消灭,和它们一起被淡忘的还有这段悲伤又令人愤怒的往事,但我觉得,这段往事不应该就此被遗忘,它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铭记在心,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他们为长江鲟类家族建了一个“诺亚方舟”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简宏妮 4月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的 “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现场,中华鲟从放流通道滑入长江 曲焕韬,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站长,从2013年至今已驻站工作了10年。
该放流站由中华鲟研究所负责日常运行管理,每年鱼类繁殖季期间,曲焕韬就会和同事及市民一起,来到宜宾市区的长江边,将人工繁育的珍稀特有鱼类苗种放流到长江自然生境。
800多公里之外的宜昌滨江公园,杨菁闲暇时常和家人在江边漫步。
“总是能看到江里成群的小鱼,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江豚跃过水面。
”中华鲟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0月5日,市民在湖北省宜昌市滨江公园灯塔广场游玩(肖艺九/摄) 位于湖北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隶属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是我国首个因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立的珍稀鱼类科研机构,是三峡集团水电开发中鱼类物种保护的技术支撑、水环境保护的创新平台和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的科普窗口。
三峡地区素有长江流域“绿色宝库”“物种基因库”之称,长江宜昌段也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中华鲟的栖息场所。
“鱼博士” “我们基本形成了以水产养殖技术研发、珍稀特有鱼类物种保护和水生态修复为三大学科方向的科研体系。
”杨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有时会去养殖车间喂养属于她的实验鱼。
2017年3月,杨菁从西北农林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毕业后,来到中华鲟研究所物种保护研究室,负责中华鲟人工种群遗传管理和生长发育调控研究。
“从事中华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似乎是一种天意。
”杨菁说,硕士期间,她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博士毕业论文跟鱼类相关。
目前,该研究所有固定科研人员63人。
比杨菁早7年来到研究所的杜合军,毕业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是中华鲟研究所物种保护技术学科组组长。
杜合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读硕士时就开始研究鱼类,那时候去野外做鱼类调研,发现很多鱼类资源受到破坏。
博士毕业的时候,从事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的人比较少,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于是便选择了这个方向。
” 杜合军初到长江三峡流域进行环境保护研究工作时,环境十分艰苦。
“当时三峡大坝上,只有1个临时的中华鲟繁殖基地,我在上面进行了2年的养殖工作。
当时,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实验条件。
”杜合军说。
9月,杜合军和同事成功完成了中华鲟的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
该项目历经十年,终于成功结案,意义重大——“类似于建立了中华鲟的基因北斗导航系统,为中华鲟种群管理和亲子关系鉴定提供理论基础,为更好地开展中华鲟等鲟形目鱼类的基因组学、遗传育种、种质保护、多倍体进化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数据支撑。
”杜合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被称为“长江鱼王”。
中华鲟是典型的长距离海河洄游性鱼类,每年6月之后,它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次年秋冬季节,到达长江中游的产卵场,进行产卵繁殖。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给中华鲟洄游产卵带来阻碍,再加上过度捕捞和误伤等,洄游到长江的野生成年中华鲟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的2000多尾迅速衰减到如今不足1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中华鲟保护工作变得刻不容缓。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特有珍稀鱼类保护技术的研发和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姜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中华鲟研究所共有12名博士,姜伟也是其中之一,他和杜合军同一年来到中华鲟研究所,挑起最为艰苦的中华鲟野外生态监测重任。
繁育 相比较后来加入的“鱼博士”,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实验站站长朱欣与中华鲟打交道的时间更为久远。
1991年,朱欣就加入了中华鲟研究所负责幼鲟培育。
1月11日,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实验站珍稀鱼类养殖车间 最初,在朱欣的心目中,中华鲟是娇弱的。
尽管亲鱼一次产卵可达30万—130万粒,但产卵后5天内,自然界只能有不到10%的鱼卵能孵化为鱼苗。
在鱼苗的养殖环节,问题又来了:尽管水取自长江,水温也跟野外保持了高度一致,过程中哪怕小心翼翼,但鱼苗的存活率却仍然只有1%—10%。
食物也是一个难题。
研究人员从江中捕来水蚯蚓、蚊幼虫和小鱼虾,它们所携带的细菌会导致鱼病。
此外,中华鲟在池底游动,娇嫩的肚皮极易被擦伤。
伤口虽然在显微镜下难以发现,但也容易感染。
朱欣回忆,1994年,研究所为准备研学活动,布置了玻璃缸鱼苗展区,幼鲟竟表现得很是活泼。
很快,鱼苗从水桶、水盆、水泥池中“搬家”到玻璃缸,开始扭尾游动,努力长大。
为了防止中华鲟娇嫩的肚皮被擦伤,朱欣和养殖人员降低了水缸中鱼苗的密度,又慢慢将水温升高,发现鱼苗们适应得更好,存活率更高了。
“我们原以为将鱼苗生存的环境控制得跟自然环境一样,它们就能活下来,其实并不是的。
这是一点一点试出来的,没有先例可循。
”朱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解决了水质、水温、鱼病、养殖设备等一系列问题后,中华鲟研究所在国内率先突破大规格幼鲟的培育技术,将规模化培育幼年中华鲟的成活率提高到70%以上。
不同于其他生物具有第二性征,中华鲟从出生到成年都不能从外形直接鉴别性别,这不利于人工养殖中华鲟的种群繁殖及放流性别比例调控。
“以前,只有成鱼才能通过穿刺的方式鉴定性别。
”杜合军介绍,2020年,中华鲟研究所研究出DNA分子性别鉴定技术,对于刚出生的鱼,只需从身上刮一点体液或者剪鳍带,就能鉴别雌雄。
对于曲焕韬来说,圆口铜鱼是他这10年来“最深的牵挂”。
曲焕韬所在的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主要承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圆口铜鱼、岩原鲤等鱼类的研究保护和增殖放流工作。
“年之前,圆口铜鱼的规模化繁育进入了一个徘徊阶段,主要制约因素就是小瓜虫病。
小瓜虫病传染性强且死亡率高,一旦暴发,短时间内会造成大批量死亡。
”曲焕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通过反复的实验,综合运用环境调控和营养免疫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小瓜虫病的防治难题终于被解决了,近年来圆口铜鱼规模化繁育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中华鲟研究所的展厅里,120多种长江特有珍稀鱼类蔚为壮观,杨菁介绍,这是全国收集驯养长江鱼类最多的一个展厅。
“长江中的鱼类总共是400多种,它们构成了非常珍贵的长江鱼类活体种质资源库。
”杨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中华鲟研究所宜昌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养殖车间,中华鲟、长江鲟和其他鱼类在蓝色的大缸里自在畅游。
朱欣说,每天都有专门的养殖工人投喂并监测它们的健康状况,每年都会给它们进行健康体检。
该保育中心于2020年正式投入使用。
现在,保育中心人工繁育中华鲟的规模已突破了1万尾,其中,成熟和近成熟中华鲟有1000多尾,这里是鲟类家族的“诺亚方舟”。
截至目前,中华鲟研究所累计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超过500万尾,为补充中华鲟种群资源、实现中华鲟可持续繁衍生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鱼类的人工繁育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野外物种的恢复。
”朱欣说。
追“鲟” 在宜昌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每年都会有中华鲟和其他长江特有珍稀鱼类被放流。
,放流的中华鲟数量有20万尾。
放流之后,通过中华鲟身上携带的各种各样的信号标记,工作人员对它们的整个轨迹和行踪进行监测。
同时,在沿江各城市设置不同的监测点位。
根据往年的监测情况来看,中华鲟会在1个月之后抵达长江口,从那里入海。
在整个过程中,渔政、航道等部门也会密切监测放流动态,让中华鲟的归家之旅能够一路平安、一路畅通。
“为了研究中华鲟放流后的洄游规律,我们对放流鱼进行标记。
对30厘米左右的小个体鱼,我们采用可视荧光标记,主要是用来区分放流的个体与可能存在的野生个体;对60—70厘米的个体,我们采用PIT芯片标记;对部分1米以上的大个体,我们将开展声呐标记。
”姜伟说,“这样标记区分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详细的中华鲟洄游数据,包括最后的入海率等信息。
我们还将对所有的放流鱼建立遗传信息档案。
” 姜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之后,长江干流中华鲟放流后的生存比例得到了大幅提升,入海比率从30%—40%提高到现在的70%左右。
但令他困惑的是,虽然人工繁育的技术已经成熟,规模化的放流也已经实现,但从海洋中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数量却并没有明显增多。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未来需要各地区、各部门联动,推动更加系统的科学研究。
” 为了科学准确地掌握中华鲟放流群体的洄游规律,自年起,姜伟和他所在的团队首次开展中华鲟海洋生活史的系统性研究。
当被问到“如果放流的这些中华鲟能够听懂人类语言,你最想对它们说什么”时,姜伟不假思索地答道:“希望这些鱼儿能够快快跑!跑到大海里好好吃好好长,长大后早点回到长江,不断繁衍生息。
” 黄金窗口期 “‘十年禁渔’对我们增殖放流工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窗口期。
”曲焕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研究保护的长江上游鱼类中大部分性成熟时间为3—4年,禁渔十年可以让这些鱼类有2—3代的繁衍机会。
“这意味着,我们长江里珍稀特有鱼类种群数量将有望得到明显提升。
” “物种和长江生态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
对于长江物种的保护,先进的理念和正确的保护措施极为关键。
”杜合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通过不断构建完整的保护体系,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与繁殖方面共同发力,长江的物种不断增多,江豚再度回归,中华鲟人工繁育放流数量逐步增长,其他特有珍稀鱼类也许将成为长江中的常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第三年和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的第三年,也是宜昌深入开展长江高水平保护修复攻坚战,进一步筑牢长江生态屏障的关键之年。
近年来,宜昌强力推进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复绿长江岸线、整治非法码头、水质改善等措施,在护航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的同时,也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宜昌市点军区艾家镇境内的葛洲坝下至芦家河浅滩是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长江鲟、长江江豚、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物以及“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的栖息地。
该保护区作为负责中华鲟监测、救治救护、科普宣传、资源调查、增殖放流、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主要保护中华鲟的自然繁殖群体及其栖息地和产卵场,对中华鲟的物种延续和珍稀水生物保护起着关键性作用。
“长江物种的保护,首先是自然种群的保护,其次为了扩大物种规模,需要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并放到自然水域中去做补充,最后也要监测物种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况。
三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层层递进。
尽管珍稀特有物种的恢复会比较漫长和艰辛,但我们对放流后中华鲟的存活比例很有信心。
”姜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没这张合影 敢说自己在天津长大?
相传天津之地,便是由精卫填海而得来之地。
有没有和小编一样想看看高高的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 图片来源:share强宝 多数哏儿都的小伙伴一定和天塔合过影吧。
小编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组织大家春游,带领我们坐电梯到天塔上面去,为了避免耳鸣,大家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就会张开嘴一起喊:“啊…” 图片来源:銘鈊3527 不过小编最期待的就是冬天了!因为最有意思的还得是溜冰啊~天塔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天然溜冰场,小时候我妈总是不放心让我在上面玩,大概是怕我掉下去淹死... 1967年,蒋大为与孟宪宏 在水上公园竹长廊为群众免费唱歌 天津水上公园原称青龙潭,作为风景区,其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初,1951年7月1日正式对游客开放,有北方的小西子之称。
是天津最大的公园,因其有东、西、南三大湖与11个岛屿组成,所以取名水上公园。
图片来源:栖栖谷的天空 上世纪70年代,水上公园儿童游乐区里有一列全国较为罕见的儿童小火车。
它的外形跟当时常见的‘绿皮客车’一模一样,就是小一号,高度略矮。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它的车头、车厢、站台等硬件设施完全仿真,除了司机是公园员工之外,车上的列车长、乘警、乘务员,以及站台上工作人员都由小学生扮演的! 图片来源:nan宝贝儿 每个在天津长大的孩子,翻阅小时候的相册,总会有几张在天津乐园合影的照片。
图片来源:nan宝贝儿 图片来源:李小妮他爹 天津乐园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同样它也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
50后曾经陪着孩子去游玩,60后曾经在那儿谈恋爱,70后记得当时的欢声笑语,80后、90后留下了童年回忆。
还记得进入乐园的第一件事嘛,当然是先和“乖乖”拍照啦! 图片来源:_MissKristy_ 还有筑波游泳馆,小时候在这里喝过水的伙伴们举个爪!那具有标志性的超大旋转滑梯,站在远处都看得见。
图片来源:时光绘影 北宁公园的大象滑梯,又是另一个童年最爱合影的地方。
那时候,哪怕玩儿完裤子都是脏的,也还是要跟妈妈吵着把滑梯玩个够。
它旁边的长颈鹿滑梯,是大象滑梯的黄金搭档,曾经一起统领着北宁公园的江湖… 磨到发亮的波浪形滑道,从上滑下来一颠一颠的,应该算是小编小时候玩过的最高最“危险”的滑梯了。
还有儿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小荡船,可以蹲在里面左右荡来荡去,不少大人也会跟着孩子一起玩。
图片来源:工作着快乐着 现在的小朋友恐怕都不知道三毛餐厅了,那个年代,没有麦大叔,没有肯爷爷,也没有特色的主题餐厅,所以面向孩子们的“西餐厅”——三毛餐厅也就独得“恩宠”~ 图片来源:轩小舞—家有三宝 如果父母带着自己去三毛餐厅,庆祝生日或者作为六一儿童节的奖励,回来后会开心好几天! 图片来源:奥利奥 不过胆小的小编一直觉得这三毛模型长得太诡异了,每次都不敢看,让我站旁边我就哭,别人的都喜欢的不行,只有我是童年阴影...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在当年,要想拍个“艺术写真”那就得去专业的照相馆了。
小编小的时候每年都会照一次写真,大概也是妈妈为了记录我的成长吧~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还记得那时候妈妈会给我换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最经典的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会顶着同款的红脸蛋儿,额头上再点一个红点点~ 虽然铜马车和大铜钱落成的时间要比金街晚上许久,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滨江道上的网红地标。
图片来源:孺子牛 很多天津人都应该记得吧,多年以前甚至是小时候的自己也曾骑着铜马车照相。
图片来源:小侠客 大孩子能在家长的帮助下坐到铜马的背上,铜马驼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背上磨得滑溜溜。
小一点的孩子,铜马太高爬不上去,就坐在铜马车上~ 那时候 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智能手机 相机也还是个稀罕的玩意儿 而纪念的方式就是在各大景点 留下属于我们的“游客照” 图片来源:清梅甜酒 小时候 总觉得日子很长 长大后的我们翻开相册 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 甚至还有些想要回到过去 是啊,你在变 你身后的天津也在变 照片中的那个瞬间却被永远珍藏
声明:本网站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东西方的民俗文化,并非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
仅供娱乐参考,请勿盲目迷信。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