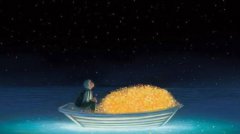林家宅37号事件真相 1956年上海的一起灭门血案
接电话的刑警赶到林家宅37号现场却没有发现人,只剩下满地的血。

后来警方怀疑一名叫叶先国的人杀害了妻儿。
叶先国抓捕归案后被定义为灭门杀人案,在官方档案里面叶先国是杀死全家后自杀身亡。
林家宅37号后来改建成了所谓的2万户房子就是工人新村,但是事件却成为轰动的灵异事件,案件至今没有结果。
查了一堆书籍,发现所有的记录都是相似的,被人为的加上了一些吓人的东西,但这个事件本身确实让人害怕。
以下应该为网络上最标准的描述了:小时候隔壁住着一个老刑警,由于年轻时候牵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80年代初就提前退休了,他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据他说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里面都找不到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后来和一些那个年代的老人询问,有些事情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老刑警告诉我有一个案子一直非常奇特,而且延续了很多年。
整件事情要从1956年武宁路灭门血案说起。
1956年的武宁路还是农田和一些沿街面的农宅以及一些工厂的仓库,老刑警说那里那个时候属于人烟稀少,晚上基本很少有人活动,那个时候那里刚刚属于普陀区,区政府刚搬到普雄路没有多少时间,他作为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被分配到了刑警,就是在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有个小住宅区,当然那个时候住宅区就是些茅草房的村落而已。
一天晚上他值班,半夜的时候电话响了。
电话里面开始是喘息声,然后有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说自己杀了人,是来投案自首的,那个声音非常奇怪,而且电话里面杂声很大。
那个年代私人电话很少,一般都是厂里面或者公用电话,但是公用电话这个时候基本也打不到了。
当时刑警就问电话里面那个人在哪里,他说就在公安局隔三条街的一个住宅区。
刑警感到情况很严重,就马上报告了值班的局长,同时通报了当地的派出所。
于是局里面能马上调动来的几个刑警都出动了。
那时的路面很坑洼,他们是坐着三轮摩托去的。
来到那个住宅区,此时黑漆漆一片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一个老刑警就问那个接电话的刑警是哪家,刑警说是林家宅37号。
打着手电筒找到37号,只见是座本地房子还是砖墙的。
推开外面的木板门有一个小院子,那个刑警回忆说刚进院子,就看到一个个小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气氛十分古怪,刑警大声问屋子里面有人伐。
但是没有人回答,屋子里面也没有亮灯。
推门发现木门被从里面顶住了。
这个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
他们照例了解了下情况。
原来住这个屋子的主人解放前逃到台湾去了,现在屋子的主人是从河北调到上海来工作的一个男人姓叶,家里四口人,姓叶的老婆是个瘸子,两个小孩一男一女。
这个时候老刑警说要找东西来顶开门。
小刑警说不如敲玻璃窗进去。
老刑警说要注意安全。
于是他们敲开玻璃窗,然后小刑警就跳了进去。
那个小刑警就是接电话以及后来转述这件事情的人。
他当时带着个手电,但是刚跳进房屋的时候没有打开。
进去以后发现站的脚下湿漉漉的,房间里面都是血腥味,又很黑小刑警非常害怕。
跟着老刑警进来了,但是落地的时候没有站稳,滑倒在地上,老刑警也觉得地上不对劲,于是站起来打开手电一看自己身上全是鲜血,小刑警更荒了,于是两个人摸索到电灯开关,打开灯顿时惊呆了。
这是间客堂间大概四个平方大小,只有张饭桌和一部童车,只见地上都是暗红色的液体,已经没到脚裸。
小刑警说这些是什么。
老刑警还算沉稳,低声说这是人血。
小刑警用发抖的声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血。
木门被打开后,派出所的同志回去打电话继续向市刑侦总队报告,留下老刑警和小刑警还有两个警察勘察现场。
小刑警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十分诡异,这栋两层楼的建筑他们上上下下找了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地上的人血到底是谁的,主人又去哪里了。
据法医说这些血起码是六个人的。
但是这家却只有四个人,邻居说这家人几个月前女的就带两个小孩回娘家了,男主人也好几天不见了。
那么半夜报案的那个人又是谁。
大概事发后一个月左右,有一天派出所民警得到居委会的人报告,说几个小孩下课的时候闹着玩发现林家宅37号的门是开着的。
大家都知道一般这种现场都帖着封条的。
而且那家的男主人经过调查也确定失踪了。
调查组还去过那个女主人的老家,也都说根本没有回来过,所以除非是主人回来要么就是小偷进去过了。
邻居也都知道那里发生奇怪的事情所以是不会进去的。
专案组就派了小刑警和当地派出所的同志一起前去查看。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进入屋子的时候发现和那天晚上一样,地上依然都是黑色的人血,而且小刑警听到二楼有小孩子嬉笑的声音,那个时候接近中午,小刑警当场有点蒙了,一起去的派出所的同志也露出惊愕的表情,他们奔上二楼,却发现原本在底楼的童车就放在楼梯口却空荡荡根本没有人。
回到局里,小刑警如实汇报了情况,大家都很纳闷,那个时候正好碰上运动期间,大家觉得古怪但是都没有说是否是鬼怪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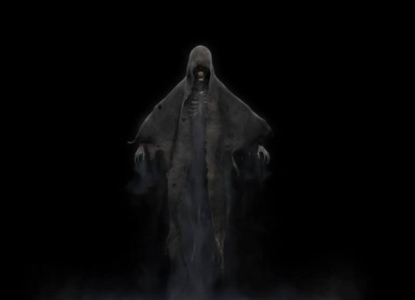
大概过了十天左右,派出所的同志说据邻居反应林家宅37号昨天晚上二楼亮起了灯。
于是专案组领导说这不是鬼怪说不定这个地方是什么特务的据点,决定夜晚守候伏击。
那天晚上十分阴冷,大家埋伏在房子周围。
到上半夜的时候二楼亮起了灯光,与其说是灯光更像是火光。
于是领头的刑警示意大家进入屋子,留了两个人在外面以防特务逃走,于是三个人进入了屋子,小刑警也是其中之一,进入屋子后屋子里面没有奇怪的血了。
他们悄悄走上二楼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身后的门关闭了。
第一个上到二楼的是姓黄的刑警他突然很回头看着跟在后面的小刑警脸上表情非常恐怖,小刑警上去一看,也愣住了,二楼和平时非常不一样完全是大户人家客厅的样子,还有张很大的餐桌,从餐桌上垂下一条雪白的手臂,手臂上还淌着鲜红的血,正滴到地板上。
走在最后面的刑警突然说有鬼,小刑警回头看到什么东西正拖着那个刑警,那个刑警露出惊恐的表情,小刑警吓得腿都软了,这个时候突然还听到老式留声机的音乐还有孩子的笑声,他事后回忆当时非常慌乱,多年后我还能从他眼神中体会出当时的恐怖,他们当时都没有打手电,小刑警回忆说当时二楼非常亮,他们只看清那条手臂,突然灯火灭了,房子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留在门外的人后来说在外面等了十分钟只听到里面一直没有声音于是就冲进来了。
当时一起进去的三个刑警却只剩下两个人,那最后上楼的刑警不见了。
事情开始更加严重。
当小刑警后来回忆灯火灭了之后到外面的人闯进来中间那个时刻他觉得有一个红影子在眼前一晃而过,而那个失踪的刑警也惨叫了一声,后来人进来手电筒照亮的时候他只看见在他前面的那个刑警和他却是躺在客堂间里面。
那个时候分局和市里面的刑侦专家还有华东军分区和公安部的专家都秘密来这里进行勘察,但是整座房屋并无奇怪的地方甚至连什么暗道和夹墙之类的都不存在,所以特务是排除了。
那么那个报案的是谁,当时技术没有现在发达所以也无法查证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那个失踪的刑警后来就通报为因公牺牲作罢,但是这件案子作为悬案一直放着,因为实在太诡异所以当事人也纷纷调离醒队,之后几年只有小刑警还留在刑队,另外一个老刑警经过那次的事情后精神一直不太稳定也提早病退了。
局领导要求对外严禁说出那晚的事情。
林家宅37号之后一直无人居住,白天甚至都没有人赶接近那里。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1958年冬天,群众举报了一个反革命分子。
这个人姓许,平时是个皮匠。
经过查实这个许皮匠是个一贯道分子,所谓一贯道是一个反动封建道门组织,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反动组织,但是在江浙一带却有不小市场,所以危害很大。
当时上海一贯道分子还是属于比较稀少,据说一贯道类似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其中有不少拥有奇术的人。
会以符咒治病,当然那个年代破除四旧很少有人相信他们这套鬼话。
在这个姓许交代的一贯道上海组织人员名单里面却出现林家宅37号男主人的名字,当时就引起了重视,时隔两年后林家宅37号的事件再次浮出水面。
姓许还交代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林家宅37号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许皮匠曾经和37号的主人见过面。
那晚提审室空气异常凝重。
参与审讯的人从半夜一直问到第二天中午,出来的时候还很气愤的说这个死硬的反革命分子简直胡说八道。
小刑警当时是没有参加审讯,但是多年后他曾经调阅了当时的笔录。
审讯员问你当时在哪里看到叶先国的(37号的男主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许皮匠说:我小时候就认识叶先国,那个时候是民国13年。
审讯员说胡说叶先国身份证上是1933年出生的怎么可能那个时候你们就认识。
许皮匠说发誓是那个时候在河南伏牛山他的家乡看到叶先国的。
最近看见叶先国是在1956年的11月在玉佛寺。
审讯员又问,他都跟你说了什么,他在你们里面属于什么身份。
许皮匠说叶大护法早就退出一贯道组织了,我只是打了个招呼,他竟然一点都不老而且比我认识他的时候更年青,但是他脸上有个痣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
许皮匠的留下的记述就这些,那个叶先国竟然是护法级的人物,那么叶先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许皮匠到底说的是否真实,这件事情在一个月后许皮匠在看守所突然暴毙之后又蒙上了层层疑云。
许皮匠的暴毙也十分奇怪,当时同屋的三个人异口同声说许皮匠那天晚上一个人对着墙壁说了很多莫名奇妙的话好像在争论后来又好像在哀求什么人,他们都当许皮匠发神经病了,第二天醒过来却发现许皮匠还是面对墙壁坐着,却已经断气了。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最奇怪的是许皮匠的脸色异常的红润。
看守所后来做了法医鉴定,也没有发现任何中毒之类的迹象。
但是许皮匠面对的那个墙壁上后来却发现一行奇怪的文字,但是一会就消失了,据同屋犯人说那像一行符咒一样的东西具体写什么也根本不清楚。
许皮匠的死无疑给林家宅37号的事件画了一个终止符号。
一个奇怪事件一个奇异的死亡,这种事情根本没有结论。
专案组调阅了叶先国的所有档案发现叶先国的父亲也叫叶先国但是这个老叶先国也没有死亡记录,那么许皮匠是否认识的是叶先国的父亲,按照许皮匠的描述他认识叶先国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差不多40岁的人了,到1956年这个老叶先国应该是70多的老头,而绝对不可能是30十多岁的叶先国。
疑问越来越多。
于是专案组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一方面在上海秘密通缉叶先国,另外一方面派专门小组去许皮匠的老家伏牛山调查取证。
伏牛山是当年李自成出没的地方,据说有龙气,解放之前也是盗匪出没,传说伏牛山中有很多盗贼留下的洞窟,当年一贯道在伏牛山地区也是非常猖獗,山中也有一贯道设下的法坛之类的遗迹。
解放之后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加强以及解放军的多次剿灭,伏牛山恢复了少有的平静,许皮匠那个村庄就位于伏牛山外围一个叫许家口的地方,这个村子里面只有10来户人家,所以调查范围不大。
小刑警也参加了这次取证。
来到许家屯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有许皮匠这个人的存在了,因为许皮匠的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但是村里老人说许皮匠家里祖上原来是从河北霸州迁到这里来的,听说也是大户人家,后来许皮匠的爷爷迷恋道术,突然就迁到伏牛山这个小村落来定居。
调查组问了一些关于叶先国这个人的事情,有一个老人说他记得这个人,不过当时这个叶先国据说是风水先生和许皮匠的爷爷是老相识还是同乡。
叶先国的祖籍的确是河北霸州。
临走的时候老人说你们应该去许皮匠家里去看看。
许皮匠的家里位于一个小山岗之上,由于多年无人居住,远看还看得出这是这个小村庄比较华丽的建筑物,远看像个堡垒,专案组进入许家,房屋多数已经残垣断壁,一个细心的女同志突然在远里的水井圈上看到雕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
专案组并没有宗教方面的专家,于是拍摄下来,等回上海再做结论。
专案组和上海通了电话决定还是去一次河北霸州。
看看叶先国和许家到底是何种渊源。
专案组来到河北霸州,根据档案馆的资料,专案组发现叶先国的父亲的确叫叶先国,但是叶先国的爷爷确也叫叶先国,而且叶家不是什么大富之家,却是历代在一个叫玉皇庙的地方做庙祝的。
档案其他资料都是叶家族谱中的一些记载,却对于叶先国这个人记述不多,也没有发现一贯道和叶家有什么联系,小刑警说她当时一起帮助查询资料所以闲着无事也就对于其他人不注意的一些档案记述多看了几眼。
原来叶先国的祖上从明朝末年就来到霸州承继了玉皇庙的庙祝这个职位,玉皇庙庙祝这个职位在明代却也有从四品这样一个法衔。
玉皇庙开山祖师据说是北方道教修仙派刘志明的一个弟子。
而这个刘志明却是明朝中叶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据说他得到过三卷九天妙法,根据这个妙法人可以修仙得道并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当地地方志就有叶先国先人在霸州祈雨得雨的记载。
当然小刑警对于这些记述只是当民间传说看待。
专案组在霸州的调查没有很大结果,反而给叶先国这个人的身世更笼罩了一层迷一样的色彩。
这个时候上海指挥中心来电话,据说最近有人在江西龙虎山附近看到国叶先国,而上海林家宅37号据说最近又有一些怪事发生。
于是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去江西龙虎山,一路回上海继续跟踪林家宅37号的进展。
小刑警随队赶回上海,才了解到,原来当时林家宅附近开始兴建工人新村,工人在拆迁林家宅37号的时候在地下3米处挖掘出一个大缸,缸里面竟然是失踪的叶先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市刑队在时隔两年后终于将林家宅37号事件定性为重大刑事案件,看来叶先国杀妻灭门罪名完全成立,于是向全国发出A级通缉令。
小刑警去再次去事发现场,只见林家宅37号已经夷为平地,而那个挖掘出大缸的地方竟然就是原先的客堂间的位置,但是林家宅37号很多的谜团还是没有解开失踪的刑警去哪里了,原先房屋中种种奇异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只有等叶先国抓捕归案后才能一一解开。
两个星期后江西小队在江西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成功的在江西龙虎山一个破败的道观遗址附近将叶先国抓获并解送回上海。
由于叶先国案件的特殊性,他被关在提篮桥一间特殊的单人囚室中。
由公安部派出的审讯专家对其进行审讯。
法医鉴定组的老陈却告诉小刑警一个在解剖叶先国妻儿中发现的问题,解剖时他发现叶先国妻子和儿女竟然毫无腐败现象他当时说简直就像活人,但是却毫无生命迹象。
根本不像死了两年多的。
尸体要等叶先国审结后再送火葬场。
叶先国被押回上海后审讯中也出现问题,叶先国整个人象得了某种精神疾病,也根本不说话,问他什么他只是眼神呆滞看着天花板,并且他回上海后一直没有进过食。
甚至连水都没有喝过。
一个月后专案组和公安部专家毫无头绪。
这个案子毕竟已经进行了快三年,叶先国先后被进行了三次不同层级的精神鉴定,在一次照x光中,当时在场的人差点都吓个半死,因为叶先国竟然没有脑组织。
一个没有脑组织的人根本就不是人的概念,叶先国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问他这个案子就这样终结了么。
刑警说后面的事情就是秘密了。
但是知道的人基本就剩我了。
那是最后一次带叶先国去指认现场,那是1959年的4月的一个晚上,他记得第二天就是清明节,他们回到林家宅37号旧址,那晚上海风力不小,甚至有点迷眼,来到已经成为废墟的37号时。
突然叶先国哈哈大笑起来,那种笑非常诡异。
当时突然整个进入旧址的人发现周围竟然泛起一层迷雾,在四周负责警戒的武警战士也发现根本无法看清37号废墟中的刑警和叶先国等人。
小刑警说那晚他也在外围,看到这个情况他就想走进迷雾那端去看看情况当他走进去的时候发现迷雾中竟然有若干金光,虚浮在迷雾中而且很多,他告诉我那些就是符咒,你根本无法靠近这些符咒。
迷雾散去后,叶先国不见了,进去的三个刑警中都已经昏迷,后来据昏迷的刑警回忆,他们看到迷雾起来后,用枪顶住叶先国,然后他们看到令人恐怖的景象,已经拆掉的37号竟然又出现了,他们竟然还是在那个客堂间里,而且二楼又传来孩子的笑声,当时他们看到叶先国仿佛飘走一样竟然走入了墙里面就不见了,当时他们马上向墙里射击,但是墙里竟然出现一股很大的力量将他们瞬间击昏。
这些口述刑警说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所以叶先国最后被定义为灭门杀人案,在官方档案里面叶先国是杀死全家后自杀身亡。
那么叶先国究竟是什么人,老刑警说他有个好朋友非常喜欢看古书,当时他问过这个朋友,这个朋友说这个叶先国不会就是古时候那些修道成仙的人吧,也许叶先国根本不是40岁而是一个活了很久的人,他的妻儿本来也应该和他一起成仙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尸身不腐。
刘志明得到的那三卷九天秘法也许就传给了叶先国。
至于那些奇幻的现象也完全可能是道术中的障眼法,至少叶先国是擅于用符箓的一个法师。
叶先国消失了,也许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林家宅37号后来改建成了所谓的2万户房子就是工人新村。
前队友赞于汉超:和你做过队友又还在一个房间绝对能吹一辈子
老将于汉超下半时替补登场后打进一球,赛后他的前队友朱晓刚也为他送上赞美。
朱晓刚发布了曾与于汉超一起效力时的照片,并开心地说道:“猴王猴王,能和你做过队友又还在一个房间绝对能吹一辈子牛逼。
” 朱晓刚和于汉超曾经是大连阿尔滨的队友,此后于汉超辗转广州恒大和上海申花,至今仍活跃在中超赛场,且在队中仍有重要作用,而朱晓刚的职业生涯较为平淡,目前已经退役。
(注:新闻图片取自朱晓刚微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舞剧《咏春》:以舞辅仁
2024年春晚,《咏春》精编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惊艳登场。
2024年度文化传播 它是一个无需语言就能让观众“读”懂的故事,它是一次结合多种艺术形式和文化样态的绝妙尝试。
它融合了俊朗武术和飘逸舞姿,结合了舞剧精髓与武术精神。
它删繁就简,以小见大;它写意又写实,极简又宏阔。
它不只塑造出英雄本色,还提纯了英雄精神,讲好了中国故事。
大幕拉开,“叶师傅”一袭黑色长衫,离开故乡佛山前往香港,踏入群雄林立的武馆街,想为咏春开一扇门……这是一个围绕中国传统武术咏春拳展开的故事。
2024年龙年春晚,舞剧《咏春》片段曾经让不少观众赞叹岭南风味的“舞武融合”,其实这部由深圳出品的原创舞剧,在B站2022年12月31日的跨年晚会上就曾斩获2亿播放量,拥有一众粉丝。
2024年秋天,它又走进欧洲,在伦敦和巴黎掀起了一阵“咏春热”。
《咏春》之美,美在舞武和合的视听盛宴,美在传统与现代的无缝对接;《咏春》之新,新在创新重塑传统文化表达体系,新在孵化机制够包容、传播手段够新锐。
这是一个传统又现代的故事,用“深圳文艺+深圳设计”实现“咏春拳”和“香云纱”活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用“双故事线”展现出岭南文化独特魅力和新时代深圳精神风貌的华章。
《咏春》让舞剧“潮”起来、“燃”起来,成为深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典范。
一个担负起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故事,出自深圳似乎理所应当。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作为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勇立潮头、锐意创新、追光逐梦是深圳城市品格的自然流露。
不少观众在看《咏春》前,惊讶于这出文艺大剧的出品方,不是来自北京和上海,而居然是来自深圳。
但看完这部五星佳作后,又纷纷表示“这很深圳”——“咏春”是最能展现岭南风骨、中国精神的传统文化经典IP,以“春”咏志的深圳敢于挑战这个经典题材,恰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的生动实践。
一棵古树达成的开端 能在伦敦连演12场,是《咏春》总编导之一韩真没想到的,她更没想到的是,向来含蓄的英国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尖叫不止,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让演员们数次返场谢幕。
在伦敦的每一次演出现场韩真都留意观察,第一场演出,观众里亚裔面孔占到三四成。
西方观众中,能看出来有不少是功夫爱好者,因为他们穿着当地武馆的练功服。
首场演出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即以“古代艺术、现代舞台”为题报道了《咏春》首映情况,专注于戏剧和表演艺术的专业评论网站Curtain Call Reviews给出了五星高分。
热爱艺术和舞蹈的观众迅速涌进伦敦沙德勒之井剧院,观看者逐渐多元,非亚裔面孔的西方观众占据了剧场的80%以上。
海外观众不再仅仅抱着猎奇心态看中国功夫,而是看到了人,而艺术本该如此,没有跨越不了的文化,只有跨越不了的心灵。
法鲁克·乔杜里是英国现代舞团阿库·汉姆舞蹈团的监制、制作人,也是前职业舞蹈家,他特别喜欢《咏春》中八卦掌片段——“舞者的身体内仿佛正进行一场风暴。
”他作为同行受邀观看了首场演出后,马上自掏腰包给家人买了票,没过几天,陪着朋友又观看了一遍。
在他看来,《咏春》不仅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展示了中国美学和艺术,更给观众带来了“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的观演感受,带来情感共鸣。
根据公开的票房统计,《咏春》在伦敦和巴黎的演出共16场,晚上场次的票几乎售罄,创下中国舞剧在欧洲商演时间最长、场次最多、票房最好的纪录。
不少伦敦市民“二刷”甚至“三刷”《咏春》,在英国掀起了一股来自中国的艺术风潮,也带动起了文创周边,不少观众得知《咏春》是由深圳原创出品时,直接被“种草”,在网络上留言说:“我一定要去。
”“《咏春》成功勾起了我对中国岭南地区的兴趣。
” 视频片段在YouTube上,已经有130多万播放量,收获了2.6万点赞。
有人没看够,强烈要求加演,还有人建议《咏春》来自己的城市巡演。
在英、法演出取得亮眼成绩,吸引了众多国际合作机构和承接商,他们正朝《咏春》挥动橄榄枝,积极与《咏春》团队联系,协商将《咏春》引入本地的可能性。
《咏春》自2022年12月于深圳启航以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在全球46座城市、56座剧院演出了233场。
“我相信观众会看得懂、感受得到。
”周莉亚说,“因为这部剧不仅包含为世界所熟悉的中国功夫,还传递了一种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性格特质。
我相信这也是西方观众了解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途径。
” 在创排《咏春》之前,总编导韩真和周莉亚曾深入岭南地区调研,取材、采风、查证,在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里找寻线索。
她们发现岭南文化有一种特殊的风貌,一方面传统根脉深厚,却又在这基础上,开风气之先,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
韩真到现在都记得,采风时行至中英街——这条250米长的街道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是特区中的“特区”,街中心有一棵百年古树,根在大陆,繁茂的树冠枝叶覆盖香港一方,因而构成一处奇妙的景观。
这处景观触动了韩真和周莉亚,她们开始有表达的冲动,渴望寻找一个质朴的故事去呈现这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一棵古树达成一个作品的美好开端。
在深圳电影制片厂的档案馆,她们又发现,原来大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侠港片都是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
自己那代青少年就是看这些英雄的故事长大的,而电影对武术的传播意义,不仅影响了她们这代人,更是实现了国际上深层次的文化传播。
两人灵感迸发,决定创作一部关于拍摄咏春电影的故事。
“今月曾经照古人” 《咏春》之难在于双线叙事。
虽然剧名为《咏春》,但它讲的却不仅仅是一代宗师叶问的故事,而是以一深圳剧组拍摄电影《咏春》为引,拉开全剧大幕。
电影里的“叶师傅”远赴他乡,只为开咏春的一扇门;舞台上的片场中,剧组众人同样怀抱梦想奔赴山海,为追心中的一束光。
前者是“扶弱小以武辅仁”、弘扬民族自信的英雄,后者则是根植深圳城市发展的时代脉络,致敬追光的平凡人。
一个戏中戏的结构成就了两个时代的同频共振,南下打工的大春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拼搏与剧中叶师傅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打通了两个故事之间的情感勾连和“理想”共鸣。
图/《咏春》宣传照 摄影/王徐峰 舞台剧不同于影视,无法利用蒙太奇,在一部作品的时间里,同时讲好两个时空的两拨人的故事,无论如何都很困难。
“韩周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这是网络上许多舞剧迷笑谈的一句话。
最终,通过舞美置景以及舞蹈编排的设置,从影业公司到武馆街跨越半个世纪的两个场景在舞台上实现旋转交替和场景转换,让同处于各自困境中的两条故事支线,产生了一种类似“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对照。
从而恰到好处地让观众、剧中人共同在这种对照中产生共情。
“我们实在不想去延续影视剧已经给大家划定好的一个老故事,每个时代都有对功夫不同理解,也应该有自己的表达。
”韩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且创作本身是需要克制的,这也是这部舞剧并未选取“叶问”或“一代宗师”的原因。
在韩真眼中,咏春代表着两个时代的人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这是咏春的意义所在,也是在咏春拳之外,所赋予这两个字的更广泛深厚的精神内涵。
“双线叙事”不仅拓展了舞剧“众生相”的边界,还让观众能以“上帝视角”窥见创作者内心的图景。
两条线时而分开,时而重合,所有服化、场景、灯光都随之分裂与聚合,共同构成《咏春》复杂的叙事模态。
在舞台上同时呈现两个时空,这种开创性的表达,也成为《咏春》对于重构舞台空间的一次探索。
用舞蹈诠释岭南武术精髓,是《咏春》的一大看点,也是创排的另一大难点。
主演常宏基记得,为了完美呈现武术效果,所有演员一起学武练武,由咏春、螳螂、太极、八极、八卦等拳法和掌法的非遗传承人进行指导,前后持续一年,其中打桩有三个月,最后所有演员的手腕和手肘都是淤青。
封闭式排练近半年,封闭期间,每天要进行近12小时高强度的创排训练。
后来即便进入巡演周期,演出之余,他们也做到了“拳不离手”。
让舞蹈演员学习武术动作并不难,难的是武舞结合。
因为舞蹈演员的呼吸和发力方式,与武者完全不同,要想打出真功夫,只能扎扎实实学,从零开始,没有捷径。
舞蹈动作多优美舒展,但武术需要气息下沉,将力量极速打出。
这样一来,要让武打动作与舞蹈节奏相合,就尤为困难,只能一遍遍磨合细调。
功夫对体力的消耗极大,对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掌握武术的力量感和内在气韵之后,接下来是艺术转化,毕竟舞台要求可看性。
电影里,“大战三百回合”只需镜头剪辑就能完美实现,一次做不好可以拍好多条。
舞剧可不行,舞台上所有的武术套路都需要舞蹈演员一气呵成地完成,哪怕慢半拍,哪怕有一点差错,都会导致一整套招式全部被打乱。
甚至,演员需要通过对自己肢体的控制,从而产生电影镜头的观感,例如,模拟出电影的慢镜头与停顿,在转台上去完成本该在平地上完成的舞蹈动作。
《咏春》全剧高潮舞段是叶问在群雄林立的武馆街与四大派掌门“对阵”的场面,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先后登场,叶问则以咏春拳一一破之。
所有对打套路,都要求既有武术的速度力量,也有舞蹈的飘逸洒脱,两人对攻,招式连绵不断,又不能真的伤到彼此,需要动作、节奏精准到每一寸每一秒,默契配合。
为此,所有对攻的演员都经过了“千锤百炼”。
周莉亚记得,有时候该去吃饭了,两个演员站起来,忽然“砰砰”地就“打”起来了,把所有招式对一遍,再“呼哧带喘”地擦把汗去换衣服。
有时候是排练前,一碰面,“俩人迎面走着呢,默契地就又对上招了”,过招简直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正是一遍遍磨合,才实现力量与美感的共舞,新的舞蹈语汇与武术碰撞而产生了奇妙的火花。
舞者们时而在太师椅上踢出扫堂腿,时而手持长棍纵横开阖,时而在街巷中闪转腾挪……干净利落的身手和行云流水的出招让人目不暇接,激烈对战正酣时却又点到为止,瞬时收手,拱手施礼,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古典浪漫与美感。
18分钟“通关大战”缩减为13分钟的华彩片段曾登上B站跨年晚会,累计播放量如今已经超过2.8亿。
传统焕发出了新生 人们心中的叶问坚定、隐忍,总是一袭黑色中式长衫。
舞台上,黑幕与光束之下,叶师傅的黑衫像陶瓷一样光洁,亦有黑胶唱片般的质感。
这种极具特色的布料,是韩真和周莉亚在采风时发现的岭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
“采风的时候,偶然看到在田间晾晒着的香云纱,瞬间就被打动,实在太美了!”韩真说。
作为岭南地区的一种古老染色面料,香云纱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手工工艺,以丝绸为胚,用植物和矿物染整,非常昂贵,被称作面料中的“软黄金”。
张爱玲在《沉香屑》中写到过:“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图/《咏春》宣传照 摄影/王徐峰 香云纱的黑色,在光束照下,不会像黑色棉布那样把光线吸收,而是反射出清朗的色泽,可以呈现出传说中的“五彩斑斓的黑”,幽暗却明亮,坚定又不失灵动。
如果说咏春拳可以承载故事的主题,那么香云纱刚好以视觉呈现人物的性格。
在舞剧中,香云纱不仅被用在人物服饰的制作,其制作过程也被艺术化地写进了剧情里,舞者们穿着柔滑的香云纱,极具岭南风韵。
咏春拳和香云纱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巧妙融入舞剧,传统焕发出了新生。
以当代“语言”诠释传统文化,正是《咏春》得以“破圈”的原因。
韩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舞剧中注入非遗文化,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一片有历史的土壤,一定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和非遗的传承,但是这些是否适合作品,还要看整个作品真正呈现时的需求,创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要在传统作品里体现当代性,就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回望,而是在其中注入当代的思考。
在为舞剧《咏春》采风时,韩真就透过咏春,思考过功夫在当代的意义。
在她看来,咏春祖训里“勤练习技不离身,养正气戒滥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以武辅仁”这四句话,满满透出了中国人的勤劳、温文、谦让和处世哲学,不但具有当代性,而且是可以通过舞剧与全世界分享的古老智慧,小小的招式里藏着大大的天地。
这种链接传统与现代的特性,也正是深圳的城市品格。
深植于内心的力量,自然可以跨越山海,获得更广大人群的共情。
韩真和周莉亚始终记得2023年9月《咏春》首度走出国门,首站登陆新加坡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在观众席的前区,有两位老人,他们全程绷得板直地坐着,到了演出后程的时候,甚至攥紧拳头,演出结束后,他们又站起来鼓掌。
后来,韩真听说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早早从岭南地区下南洋,背井离乡出去打拼。
在《咏春》里,他们看到叶问,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更感受到了故乡。
韩真记得,那天还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大使,其中一个大使对她说:“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
” 没有什么力量比情感的共鸣更强大。
《咏春》不仅用新的舞蹈语汇与武术碰撞产生的美感吸引了不同国家的观众,将传统文化在今天语境中创造出新的解读,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探索了一条新路。
“我们渴望英雄,渴望塑造自己民族的英雄,渴望证明自己,所以英雄在功夫这个概念里留下了印记。
从今天看,英雄是什么?谁是英雄?也许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了生活和理想而努力的普通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英雄。
”韩真说。
《咏春》不仅致敬英雄,也致敬每一个在生活里怀抱梦想的普通人,当大幕落下,舞台幕布上缓缓闪动着一句话:“英雄站在光里,而我们愿是那束光。
” 发于2025.1.6总第117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舞剧《咏春》:以舞辅仁 记者:李静 编辑:杨时旸
声明:本网站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东西方的民俗文化,并非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
仅供娱乐参考,请勿盲目迷信。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